几年前,母亲突然因病去世,悲怮的我们在料理完母亲的丧事后,就跟父亲商量着接他进城,和我们一起生活、安度晚年。
可是父亲却看着母亲的照片摆摆手:“这个家不能没有人守着,我现在身子还硬朗,能做饭会种庄稼的,闲了还可以和村里的老伙计们聊聊天、无玩花牌,你们那城里边呀,楼那么高,憋得慌,不去!”
从那以后,父亲便一个人独自生活在乡下的老家。
其实我们心里知道,父亲是怕给我们增添麻烦,于是,我们兄妹便商议,不管是谁,都必须隔一段时间轮流回老家,陪父亲几日,每次回家,当兵出身的父亲把家里收拾得非常干净整洁,还会在我们到家时做好可口的饭菜等着我们,这让我们一进门就能感觉到家的温暖,我们能做的事情仅仅是帮父亲拆洗一下炕上的被褥,打扫屋子,陪他聊聊家常。
上个星期天一大早,我带着七岁的儿子从县城乘车回家看望父亲,还没迈上大门的台阶,一只洁白如雪的小狗“汪汪”叫着便跑出家门,一直怕狗的儿子躲在我身后又踢又叫:“爷爷!爷爷----”
父亲听到声音走出屋子喊“小白,一边去!”然后冲它挥挥手,只见小狗箭一样就蹿向父亲脚边,摇着尾巴,好像做错事的孩子,嘴里“呜呜”着,看着小狗可怜又可爱的模样,我和儿子不禁笑了。
吃饭的时候,父亲把馒头掰成小块,泡在菜盘子里,然后夹给小白吃,我假装生气地说:“爸,你怎么也不夹一块给我和你的外孙呀,看不下去您了!”儿子也开玩笑地喊:“爷爷是个偏心眼,不爱外孙爱小狗!”父亲看着我们哈哈直笑:“好,我的好女儿、我的乖外孙,赶快吃吧!”这话刚一说完,我们爷仨就相互大笑起来,哈哈!跟一只小狗较什么劲呀!
吃过饭,和父亲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说话,冬日午后的阳光暖暖地照着,儿子去找村里的小伙伴玩了,小白就乖乖地躺在父亲脚边,时而歪着脑袋、用它的圆眼睛时而看看我,时而看看父亲,时而用嘴巴玩弄着自己细小的尾巴,时而又站起来,冲着大门口叫几声----这时,父亲就用手摸摸它的小脑袋,它的脸就势挨上父亲的手,嘴里舒服地哼哼着,目光中充满柔情。
我和父亲聊着我的工作,聊着儿子,聊着村里的事情,后来话题便自然地转到了狗的身上。平日里,言语不多的父亲笑着说:“刚送来时的小狗肉肉的,身上的毛竟然比现在还白呢,我就喊它‘小白’了,这名字好听不?”
“好听!”我笑着回答。
父亲又接着说:“现在可调皮了,总爱出去玩,有时弄得身上特别脏,隔一段时间就得给它洗一次澡,不过,这小东西耳朵特别尖,深夜的时候,村里上夜班的人回来了,它在屋里听到村路上的脚步声,就开始汪汪叫,直到那脚步声远了,才会‘善罢甘休’,继续睡自己的睡觉,嘿嘿!”说到这里,父亲再次开心地笑起来。
阳光暖暖地照在父亲的身上,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父亲下意识地用手抓抓头皮。
“爸!头发长了,天气这么好,我来给你理发吧!”我轻声地对父亲说。
“不用不用,你就陪我说说话,我明儿个去集上理!”父亲竟然站起来,有些害羞地摆摆手。
“怎么?女儿想给父亲理个发也不行呀?”我把父亲轻轻按坐到小板凳上,假装生气地问。
“好!好!你这娃呀!”父亲哈哈笑着,乖乖坐下来。
给父亲围上理发用的塑料布,我小心翼翼地握着电推子,让它慢慢地在父亲花白的头顶上游走着,看着琐碎的头发一点一点地落到地上,理完了,我拿着镜子让父亲看:“瞧!这一理多精神呀,就跟当兵那会子一样呢!”
“哈哈!”父亲看着镜中的自己,爽朗的笑了,我端来热水,父亲弯下腰,我仔细地给他洗着,父亲的头皮硬硬的,头顶的头发也不再生长了,洗着洗着,我的眼泪不知怎么地就落了下来,我抬起胳膊,悄悄地擦掉眼泪,母亲不在了,父亲一个人该是多么地寂寞呀,可他在我们面前还是像山一样的坚毅,总是流露着快乐,他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们知道,虽然母亲不在了,但他还在,这个家也永远在,这就是我们慈祥又亲爱的父亲呀!
看着父亲脸上的笑容,听着他爽朗的笑声,我的心里一阵温暖,就像这冬日午后的阳光一样呢!
作者资料:王粉玲,陕西蒲城人,专职写作,写作体裁:散文、诗歌、儿童文学等,在全国多家刊社发表作品百余篇,出版个人专集多本,2014年获陕西作协首届(2013)年度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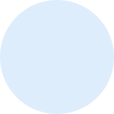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