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年父亲去世时,我远在千里之外的海南岛。
六月二十七日下午六点左右得知父亲病重的消息[父亲是下午三点左右住进的医院],心情乱作一团,我了解父亲的身体,于是并立刻去联系机票等事宜,一切办妥后已是晚上八点多钟.这是我有生以来最漫长的一个夜,无法言语的悲痛时时蚕食着我,使我无法入眠,凌晨三、四点左右更是如万箭穿心般绞痛,天一放亮并迫不急待与家中联系,顿时我肝肠寸断:父亲巳于凌晨三、四点钟驾鹤西归!
那一天是农历乙亥年六月初一。
即便时间巳过了十年有余,但每每想起,我心依旧隐隐作痛,“一缕轻烟似的悲痛盘旋在我心上,久久不灭.”
父亲静静躺在水晶棺内,当时是六月,却雨水不停.父亲身着那套生前也曾穿过的深色外套,脸和整个身躯用寿被盖着.在之后的几天里,我浸于沉默与悲伤之中,整天昏然若失.出殡前夜,我将所有亲朋都安排去休息,只留下自己一个人,一人独自坐在灵堂内,默默陪着父亲,陪着一位为了我操劳终生、省吃俭用的勤劳老人;陪着一位为我分担一切负担压力却毫无一丝怨言的慈祥老人;陪着一位为了我可以付出一切、临终儿子却为生计远在千里之遥无法为其送终的善良老人.
父亲的灵堂设在单位住宅区内的水泥坪上.外面飒飒地下着雨,灵堂的帐篷有几处开始漏雨.我尽全力不使雨水流入灵堂,但一切努力最终无济于事,灵堂的地上开始有了水,我身上也有些淋湿,但水晶棺四周却无一丝水滴.我终于放弃了一切努力,任凭帐篷在风雨中发出颤抖地哭泣.
搬来一条长凳,我伏靠在棺木旁,无言无语地坐着,簌簌流泪.我渴望能最后聆听一次父亲那熟悉地鼾声,想最后一次感觉父亲脉搏的跳动.在意识之中,总觉得父亲会有重新坐起来的那一刻,然后象十多年前的那个深夜,当时为我们装运柴火的车辆在跑上坏了,司机回家去取配件,在那前不着村后不落户的郊外,就我们父子俩,在淡谈月下谈论着我热爱的文学.
父亲静静躺着,六十三年的奔波,也许他真的累了!
我,也就这样默默坐着,陪着与我共同生活了三十一年的父亲,陪着他走完他最后的路程.
次日的追悼会上,雨依然下个不停.当盖在父亲脸上的寿被被缓缓揭开,我看见他老人家微微睁着的双眼流露出临终前未能最后见到自己的儿子一面所留下的无法弥补的深深的遗憾的神色.据去医院看望过我父亲的同窗说刚入院不久的父亲曾对他们说过要让我赶回来,但我却最终还是未能了却他的心愿.父亲的双眼缓缓闭上,我的润泪水又一次忍不住夺眶而出,我将头别向一边,不敢让泪水滴在父亲的脸上---因为按本地风俗那会让父亲满身牵挂,不能安心而去.
快到出殡之时,雨突然停上---众人说这就是吉人天相!
父亲就这样走了,离开了他爱和爱他的亲人,去了那个神秘而又永恒的世界,回到了生命的源头和真正的归宿.
不管用多么隆重的仪式祭奠父亲都无法表达我内心万分之一的悲痛,我唯一可以用来纪念和安慰父亲在天之灵的方式是通过自己的发奋努力而让自己的家人活得更加幸福,更加美满快乐,这是父亲所期望的,也是我不可推卸的责任!
父亲睡在爷爷奶奶的身旁,想必不会孤单.我常独自去看望他们[即便打工在外,只要回家休假,也从不会忘记],一个人,静静坐在坟前,虽然阴阳相隔,但我却坚信我们之间能够有着跨越时空界限的心灵的沟通!
我曾问过母亲,说父亲可留下什么遗言,母亲说父亲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别忘了给剑喂药!剑是我的儿子,当时有点儿感冒,父亲是躺在医院病床上对身边的母亲说这句话的,之后父亲并再也无法言语了!
若干年前,我一岁零三个月时,负责我起居生活的奶奶在厨房作饭弄鱼,我坐在一旁,突然奶奶高血压病发了,众人忙乱一团,我可能是被当时的情景吓坏了,大哭起来,奶奶看了我一眼,轻轻说了句:“黑仔,莫哭.”黑仔是我的乳名,“黑仔,莫哭.”这短短四个字成了奶奶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声音!我不可能能在脑海中留下当时的记忆,但我可以想象得出奶奶最后投向我的那充满慈祥和仁爱的目光
奶奶与父亲的遗言听起来都几乎是那么的平淡,但其中所包涵的深深爱意与浓浓的亲情却令我铭刻于心,永远永远不能忘怀,直至我生命终止.
面对爷爷奶奶与父亲的遗像,我内心深处总是有一种痛,那是一种无法用言语所能表达的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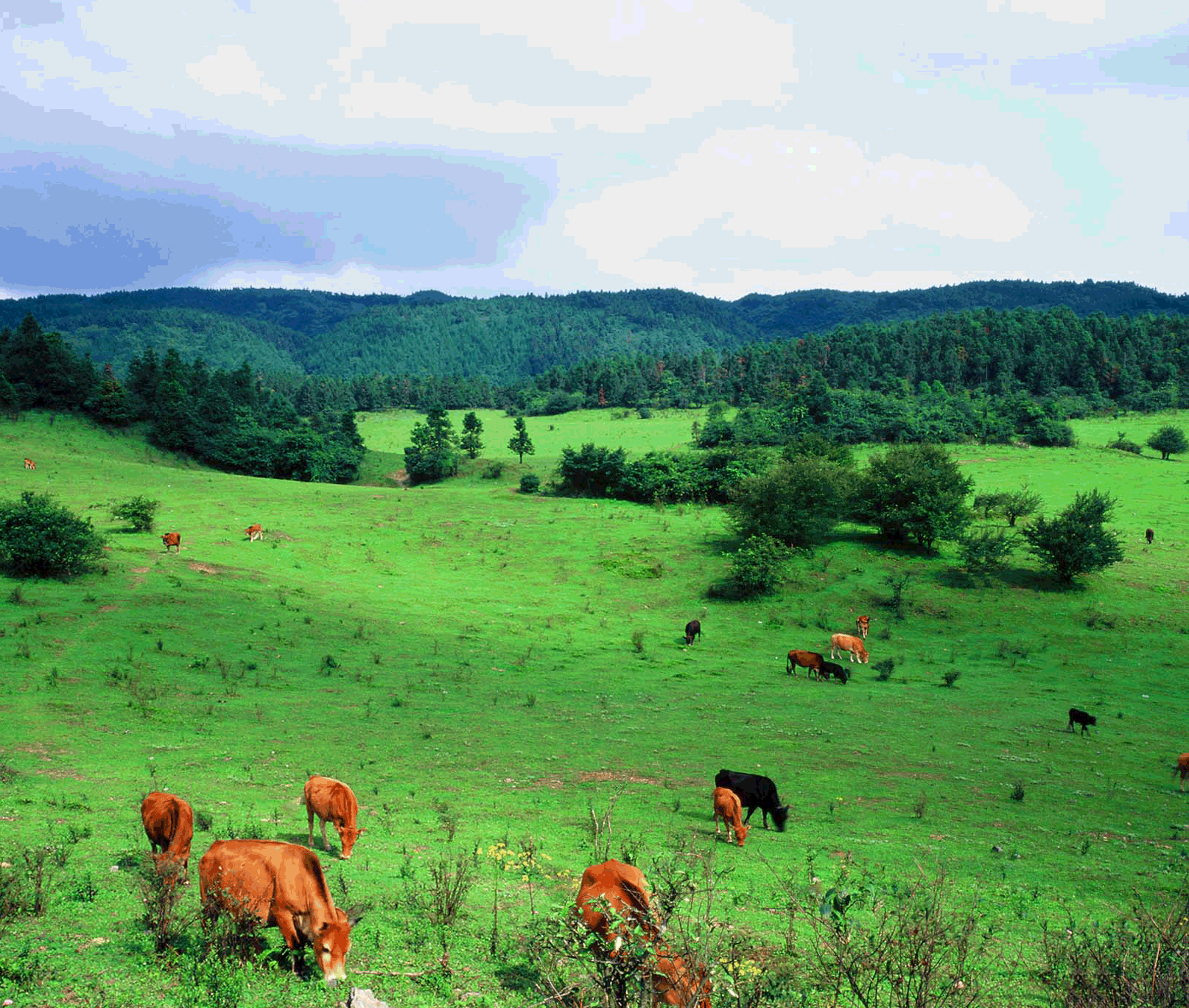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