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古楠,是一个响雷从贵州道真县那边的大山梁上搬来的。六十八岁的村医生丁天友,身板硬朗,神乎其神说起古楠,一头灰发铺满了蓬生的阳光。
山坡下是浩口乡邹家村吴家坝丁家沟,海拔一千四百米。在灌木竹林缭绕的沟坎上,九棵翠伞撑天的古楠树,恰似一群闲坐在坡坎边摆龙门阵的老翁老太,勾腰驼背,交头接耳,如胶似漆。
古楠树稀少,古时是修造宫殿之木,我从没见过。这初夏的上午,古楠哑谜一样蛊惑我。迎着艳阳,沿着羊肠盘曲的社道路,紧跟丁天友下坡,我想打探岁月与深山的沉寂,倾听古楠滴水成音的清脆。
绕过两道坡,就是柿子坪。柿子坪没有柿子树,有路边小山坳一座独家农院。后山峁上,一棵壮硕枫树,葳蕤繁茂,激情四射,独傲四野。我在意的却是路坎下一棵约三十米高,两人难抱的古楠,它犹如一缕不绝的香火,攀越在岁月之上。
路边坡坎有数米高。坎外的乱石凼,灌木藤蔓参差披拂,古楠的树身缠满了绿藤。几棵碗口粗的楠树,昂扬繁盛在古楠的树荫外。楠木的花期在四五月,树叶里圆锥花序,伞簇花蕊,馨香四溢,蜂鸣蝶舞,煞是惹人爱。楠木的果期在九十月,椭圆细果,随秋风成熟,树叶里雀飞鸟噪,更是迷人。
这时节,花期刚过,每一棵古楠都是一个家园,浑身的绿叶比地上的草叶茂密,它们吮吸着日月的精华和风雨的琼浆,让大地静谧,让鸟儿欣悦,让人心清爽,让籽实在婴囡般梦呓。我从路边一棵楠苗上摘取了一片葱绿的叶子,轻轻揉碎,手里便是一捧清香。
楠木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著名的有金丝楠、香楠、水楠三种,以金丝楠为贵,香楠次之。这里的古楠是香楠还是金丝楠?我想到金丝楠的不菲市价,问丁天友。丁天友说,有人说是金丝楠,有人说是香楠,我也没说清。这里的古楠树龄至少在百年以上,银灰色的树皮散发出幽淡的乳香。树冠一层套一层,八九叠翠楼,层层苍翠欲滴,拽动着梳风筛雨的高贵。
柿子坪往前数百米,有一座四合院,叫童家屋基。大院古朴精致,青石坝面,龙骨石房坎,树柱板墙,木楼青瓦。正房大门敞开着,西边人家房门紧锁,房檐破漏,有些摇摇欲坠。
我有些纳闷。丁天友说,我们丁姓人家是五百年前从江西迁来的,在童家屋基上建造了这座起祖大院,院外还有一座入川起祖的老坟,古楠是丁姓家族的风水,丁氏子孙都有守护之责。这时候,正房门内走出一位佝偻老太,满头银发,满脸皱纹,满眼惊喜。我问老人高寿几何?她撸了撸嘴,比了比“八十”的手势。丁天友说,这院只剩几个老人守着,五十岁以下的人都出去了,房坏了的那家人早搬进了城。这是僻远农村的实景,城镇勾去了年轻人的心魄,除非节庆之日,村上看不见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了。
童家屋基外是一块坡林,五棵大小不一的古楠环院兀立,幼小楠苗在杂树间隐隐约约。最高最大一棵,三四人环抱不过,高约四十余米,其余一两人环抱,高二三十米之间。丁天友说,搞大集体时,生产队在树下烧火灰,把大树迎面的树身烤焦了。六年前,有一夜刮起吓人的狂风,摧折树上的一根树枝,坚硬的树枝砸坏了房屋,村上把树枝作这家人的补偿。有个生意人闻讯而来,花八百块钱买走了树枝。后来才知道,市价原来是这个价钱的十几倍。
被风摧折的残枝,横插在树腰上,演绎了生命的悲壮和情义的慷慨。我眼前树身,被烤焦的一块,已朽如老茧,宽可容人身。两边倔强的树皮每年都在滋长,但仍无法掩住伤痛的狰狞。这曾经的伤痛,是一种历史的财富,让人懂得了珍惜,学会宽容。
童家屋基到响水洞,先要过一条小溪沟,然后穿一片金竹林。溪沟,掩隐在林木藤草里,只闻潺潺水声和脆脆鸟鸣,在密密匝匝的光影里自由呼吸,不见粼粼清波和缓缓柔情,在遮遮掩掩的曲折里刀锋般闪烁。金竹林,大俗大雅,茂密修盈,温婉朗润,浩浩荡荡,间插了零星的灌木和楠苗,微风吹拂,一股撩人心扉的竹韵幽然若画,人在林中走,心若竹云飞。
竹林的尽头是一棵巨硕的古楠。古楠的树身,五个成年人也环抱不过。树身三米处分叉,三根树身依立顶天,四十余米高的树冠生机盎然,接纳着云彩的婉约,空气的流淌,时间的苍茫。丁天友说,这是这里最古的一棵楠木,相传生长了五百多年,树下有一个泉洞,一年四季泉水涓流不断,汩汩鸣响,泉水甘冽可口,有治病之疗效。看我一脸诧异,丁天友说,早些年,这里生了病的人就来跪求这里的神水,在树根下,曾供有一尊药王菩萨石像,日久天长,石菩萨长入了树身,这树就成了神树。
这棵古楠长在石坎上,肥隆的虬根,四围铺射,深扎进石缝和泥穴。在荆棘芒刺掩藏的石坎下,有流泉窸窣淙响。我没有否认神树的说法,在丁天友欣悦的语言里饱透了山里人亘古的朴实,他把神树的喜悦与我分享,此时,这个世界自然又多了一份喜悦。
从响水洞上吊脚楼,只需十几分钟的脚力。吊脚楼,原来是在吊脚楼屋基上建的一座农家独院,土墙灰瓦,一股清冽的泉水,沿竹槽盈盈而来。吊脚楼右坡上有两棵古楠,一大一小。小的,俊俏在路边,两人合抱不了,蓊蓊郁郁,亭亭玉立。大的,在杂树丛生的坡坎上,三人不能围抱,雄天伟地,高过五十米。吊脚楼泉水的源头,又是大树脚下的泉眼。大自然的灵异,真是深不可测。
丁天友说,四年前,这一大树被贵州的一个老板“盯上”。他几次三番找这里的农家密谈,愿花大价钱买树,出钱修一条社道路,直抵树下,方便搬运。每家人能分得几万块钱,让不少人动心,想撮合这美事。这件事被乡里知道,随即报告县上。县委书记批示森林公安,要用最严厉的手段,挂牌保护好这九棵古楠。我问丁天友,眼看到手的鸭子飞了,遗憾吗?他只傻笑,仿佛所有声音在他的心头瞬间沉寂,仿佛古楠收藏了自然界所有的声音。
阳光热烈,嫩蝉初鸣。九棵古楠和2015年初夏,在重庆市与贵州省交界的浩口乡,如梦境一般,烙进我此生的记忆。
古楠,一面世俗冷暖、人心黑白的镜子。
古楠,一腔人类与自然、生存与死亡的血性。

 门票预订
门票预订 武隆景区微信
武隆景区微信 武隆景区抖音
武隆景区抖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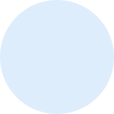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