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印象武隆》里的一个情节:一位老纤夫和一个老婆婆用重庆话讲故事,说话间说到了哭嫁。这时,舞台后边一个小楼的窗户打开了,卷帘微微上提,露出一排女孩的芊芊玉足。她们在一个无水的木盆中洗脚,然后就唱了起来——“我的父啊我的母,出嫁才知道父母的苦……”“月亮弯弯照华堂,女儿开言叫爹娘。父母养儿空指望,如似南柯梦一场。一尺五寸把儿养,移干就湿苦非常。劳心费力成虚恍,枉自爹娘苦一场……”
之所以喜欢这一段,是因为其中蕴含的孝道重重地击中了我的内心,使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一
在我的心目中,我的母亲是天下最勤劳的母亲。她就像一头不知疲倦的小毛驴,在生活这条没有尽头的磨道里,不停地劳作着。
母亲有一双关节粗大的手,而与这双手相伴的是锄头、铁锨、镰刀、扁担、井绳、笸箕、水桶、筛子、笤帚、锅碗、擀杖、面盆、针线、柴禾。这些东西成就了她的手,也摧残了她的手。有一次,母亲的右手上扎了一个葛刺,我拿一个大针帮她挑。握着她的手,我的眼睛有些湿润。这是一双怎样的手啊:青筋裸露,骨节粗大,五指弯曲,手心里到处都是老茧。然而,就是这样一双手,却是我们这个贫寒之家温暖的依靠。
母亲的手活跃在一年四季的风雨中。在田里,她会薅起一把杂草,捏死一条害虫,扶直几棵秧苗;在路边,她用镰刀割下一把嫩草,捋下几枝树叶,或者拾取一捆柴禾;回到家里,她担水,洒扫庭院,喂猪,喂鸡。她烧火,擀面条,焯野菜,烙饼,醃制咸菜,烧红薯稀饭。晚上,家人都睡了,她点着油灯纺花,织布,缝补衣服,纳鞋底。村里人谁被尘土或昆虫迷了眼睛,也会来找母亲。母亲翻开他们的眼皮,用纳鞋针的针鼻为他们轻轻拨出,眼睛就又明亮如初了。在我们老家,一个男人只管地里的重活,而一个女人除了在田地里忙碌外,还要操持一家人的吃喝和穿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连轴转。因此,一个女人的工作量往往是一个男人的两到三倍!
母亲有两个劳作的镜头令我至今难忘:一个镜头是做鞋。我们小时候穿的布鞋都是母亲手工做成的千层底,一双看似普通的单鞋或棉鞋却要费尽母亲的大量心血。制作这样的鞋要经历描鞋样、制鞋衬、选鞋面、纳鞋底、上鞋帮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很复杂。在我的印象中,母亲经常熬夜纳鞋底。在忙碌了一天,打发我们睡下后,母亲坐在床边,就着昏黄的油灯开始纳鞋底。母亲的手上下舞动,针线发出哧啦哧啦的声音,摇篮曲一样催我们进入梦乡。有时候,针锥不利了,她就将针在头皮上蹭一蹭。有时候,针刺了手,她就把指头放在嘴里吮一吮。“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这一针针,一线线,细细密密,写下的是一个母亲温馨厚实的爱啊。另一个镜头是推磨。在我们老家,磨粮食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动。那时拉磨不是用牛或驴,而是完全要靠人力。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石磨是一只无法摆脱的白虎,大把吞噬着母亲有限的体力。母亲一边要推磨,一边还得筛面。石磨发出隆隆的低吼,罗在笸箩里穿梭游动,面尘飞上了母亲的头发、眉毛和鼻子,偌大的磨房记录着母亲半天甚至一天的单调和疲劳。
繁重的劳动,使母亲落下一个毛病:膝盖疼,腿疼。多年之后,母亲被病痛折磨得整宿睡不着觉。她伸开腿,两个膝盖酸痛酸痛;想蜷一下,腿又硬得不会打弯。母亲叹一口气,又叹一口气,那长长的叹息声在山区的黑夜里痛苦地飘荡。
二
母亲属鸡,是鸡刨命。虽然一生辛劳,但她的生活愿望并不高。
母亲的第一个愿望是拥有一所新宅子。我们家长年挤住在一所土窑洞里,这是我们家族最初的居住地,但这个宅子很不安全。下雨的时候,雨条疯狂地抽打着土墙,被泡软的泥土簌簌滑落,那声响总让我们心惊肉跳。母亲决定说服父亲先建造一所砖石结构的新宅子,哪怕每劝一次都要挨一顿骂。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争吵,最终母亲胜利了。在我们的期待里,母亲跟着父亲走向一块阳坡,起掉土层,筑开岩石,像蚂蚁一样艰难地挖掘地基了。八年时间,父亲和母亲最终完成了他们的新宅工程:石砌的墙面,砖砌的拱顶,碎石碴起的院墙,树枝扎成的篱笆门。新潮而又原始,结实而又诗意。只可惜新宅盖成只有五年,父亲就匆匆地走了。那年,我带着怀孕的妻子回老家,母亲拉着我们的手说,你爹也是急命啊,我要是不催着他盖新宅,让他一直留着一个念想,他幸许还能见见二孙子长啥样,可现在……说着说着,母亲黯然神伤起来。
母亲的第二个愿望就是希望她的子女们平安长大,她就像一个母鸡一样,用翅膀护佑着她的鸡雏们。我哥哥出生时,体质很弱,三天两头发烧。每逢哥哥病了,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我家的东邻是一个神婆,利用了母亲祈求平安的心理,就让母亲把哥哥认给神当儿子。哥哥每年生日的时候,母亲都要带着他到神面前磕头,同时供上一篮白馒头,直到哥哥长到12岁为止。在那年月,一蓝白馒头可是全家半年的细粮啊,但母亲没有丝毫的犹豫。想想也是,大山里面这么闭塞,缺医少药的,你让一个母亲怎么办?她拜一个假神也总比漫长的心灵煎熬好得多吧?在母亲看来,只要能让儿女们健康成长,学有所长,即便自己受点蒙蔽受点窝囊,也是心甘情愿的。十年前,母亲信了基督教,天眼一下子开了。母亲本来不识字,但跟着礼拜了几次之后,竟能看着本子,大段大段地唱赞美诗了,真是奇事!几年前,我回老家陪母亲过年。早晨天还没亮,我朦朦胧胧地听见母亲在祷告。仔细一听才知道,母亲是在为家庭祈福,而且是天天如此,祷告成了她的黎明第一事。母亲先从儿子们开始祈祷,一直祈及媳妇们、女婿们、孙子和外孙们,请求真主给她的这些亲人们以庇护,降下幸福降下平安。冬天的山村寒气逼人,但我此刻的心里却暖洋洋的。母亲虽然偏居一隅,但她那颗母亲的心却博大细密,纯净温暖,直达天宇。
三
这些年,我时时有一种生命的倥偬感和危机感。我们的大家庭,好比是一棵亲情树,爷爷、奶奶是包裹在最外层的那片叶子。他们被岁月无情剥落的时候,我还小,还不懂得珍惜和悲伤,因为毕竟我还被父母这层正青翠的叶子温暖地包裹着,并没有感觉到风雨的凄苦和苍凉。十五年前,父亲这片并未枯黄的叶子被岁月剥除了,他的飘离让人心痛了很长时间。苍茫时空,生命是那样脆弱。对于亲情,我们如不倍加珍视,就会成为永久的遗憾。于是从父亲去世那年起,寒假或者暑假,我都要回老家小住,尽可能多陪陪母亲。
我深深地知道,有母亲的人,心是安定的;有母亲的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也是可以有点孩子气的。尤其是在有了儿子这片更嫩更柔的叶子后,我更日渐感到一种岁月逼人的压迫和危险。儿子在快速生长,母亲却在憔悴老去。一方面是生命的损耗,一方面是生命的蔚然,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虽然如此,但我还是想在心里千万次地祈祷,希望时光之手能宽容一些,希望母亲这片苍老的叶子永远护佑在我们身边。
作者简介:王剑,男,教师。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散文诗》等报刊。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散文诗学会理事。

 门票预订
门票预订 武隆景区微信
武隆景区微信 武隆景区抖音
武隆景区抖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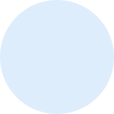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