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村庄、炊烟、牛羊和庄稼,在母亲头发上,肌肤下或手指间。
在母亲眼里,读带着颜色的声音和隐藏的乡土。有母亲的地方,童年的往事被风从遥远的岁月带来;那些相依,守护在窗前生成温暖,疗理疲惫的心。
油盐米醋,鸡毛蒜皮,简单的叙事。清水,阳光,灰尘和一些小小的苦恼是生活的本真。何必挂念月光下堆满白银的乌托邦。
何必关山万里云,有母亲的地方就是故乡。
二
雪花纷纷,像母亲从簸箕里扬下的糠,它们轻盈。让我担心,有些慌。雪花在母亲头顶,覆盖了许多年,形成她的偏头痛、失眠和眼花。雪花漫延母亲的骨头,她的关节炎、风湿病,在寒风中抱紧皱褶的肌肤和佝偻的背脊。我一阵酸楚,一阵揪痛。
雪花盛开,一片白。
在冬天,母亲是儿孙们可爱的雪人,安静地坐在角落,数着她的羔羊们。她面带笑容,仿佛流逝的光阴也如此惬意,抒情和幸福。
三
扫地的母亲低头,像一束傍晚走进粮仓的麦穗。她认真打扫安静的院坝,和夕阳余下的尘埃。她扫着我们每一个微小的动作,遗漏的语言、苦闷和随意扔掉的幸福。该拾起的拾起,该倒入垃圾池的,她一点也不含糊。
扫地的母亲,当月光洒满大地她还能否扫起,缕缕洁白的牵挂?一排露珠守望在草叶上,饱含儿时的黎明。
四
母亲睡熟时,端详她花白的头发和枯黄的面容。生活曲折,时光无情。母亲就这样在我眼前一点一点苍老下去。
她呼吸匀和,带着轻微的鼾声。多么美妙!
许多年前,母亲也这样,坐在床边,看着我把梦想一点一点铺开。
端详熟睡中的母亲,我心生恐惧,怕她不再醒来,让我成为孤儿不知该把自己放置于这个世界的何处?
五
母亲的手,冬天张开无数张小嘴,像二十年前我们四姊妹,紧紧围在她的跟前,不停地喊饿。
这松树皮一样的手,生长着寒风,生长着生活的坎坷,命运的捉弄,和些许微笑。
这砂布一样粗糙的手,不知把多少日子打磨如瓷碗光洁。
当我把凡士林药膏,轻轻涂抹在母亲手上。母亲说疼,那无数张小嘴,突然咬住了我的心。
六
母亲当民兵时,曾有学医的机会,可惜她没文化,终没成为白衣天使。
三十年后,五十多岁的母亲成了乡医院的一名清洁工。她很爱惜这份工作,从不喊累,更不说苦。
她佝偻身子,认真打扫着地上斑驳的阳光,就像打扫她那质朴而温暖的一生。
七
母亲抄电话号码时,把“7”写反了。我们始终解不开,那神秘的密码。“7”给我们,开了一个玩笑。而命运则留给母亲一生遗憾。
写反的“7”,别扭地躺在纸上,多像母亲辛酸的童年,别扭地躺在岁月深处。那时,春天曾用悲悯的目光,企图打湿她泛绿的梦。
八
杂技团演出,人很拥挤,母亲好不容易弄了一张票。
若大的帐篷,活像一个蒸笼,母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挤进去,然后又挤出来。她不是为了观看精彩的杂技。
母亲抹了一把汗,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杂技团推销的佛像,虔诚地挂在我的脖子上。
小时候,我们在母亲身前身后,母亲保佑着我们。长大了,我们翅膀丰满了,我们要远行了,母亲的心里变得不安起来。
我理解母亲的苦心,佛像不重,母爱很沉。
九
一大清早,母亲对我说,她梦见了父亲。父亲还像当年一样,那么讲究!穿着反光皮鞋,梳二分头,用洗脸帕拍拍衣上的灰尘,去赶集了。晚上回来,父亲从口袋里掏出豆腐干,我们坐在床头,像一群贪婪的耗子津津有味地啃着。
母亲对我说着,脸上堆满笑容。我一直幸福地倾听她甜蜜的叙述,而父亲早已谢世,离开我们十多年了。
十
陈旧的木床和母亲寂寞地生活,母亲从没发现自己会“认床”,大姐接她进城去住,三天后她悄悄跑回来。
那三天晚上,母亲从没合上一眼。她怕自己不小心,会永远沉睡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回不了炊烟熏黑的木屋。
或者,仿佛那个小村庄没有了她,田野会变得更加空寂,弯弯曲曲的小路,将不知伸往何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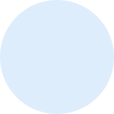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