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余晖斜射入飘窗,卧室仿佛镀了一层金。我坐于床沿,折叠洗晒干净的素色被面。细棉布吸收了阳光与秋风的温度,隐约有温暖从指尖传来,好似遥远的旧梦。
也是在深秋这样阳光和暖的日子,我的小脚奶奶总带着我同妹妹,把被子都搬到岗上堰塘边去洗。奶奶的被子是蓝色印染的家织土布,粗糙的质感,温暖贴心如奶奶长满老茧的手。家织土布打湿水很重,搓不动,得放到堰堤上木澡盘里,我同妹妹赤脚去踩。太阳是暖的,水是凉的,我同妹妹牵着手,笑闹着,踩得满澡盆肥皂泡,奶奶就在一旁无限欢喜地望我们笑。
堤上,黄艳的南瓜花正开在秋风里,瓜蔓下还卧着老南瓜。稍远一点是棉田,几朵晚开的白棉花还残留在枯枝上。也有茅草同白荻,又萧瑟,又温柔,它们一起向我们宣告着秋天万物的成熟同成熟的奥秘。
洗干净的被子就晾在堰堤竹竿上,像秋风暖阳下的一面旗帜。
这样洗晒干净的印花被子味道很好闻,有水的味道,有风的味道,有太阳的味道,还有青青菜蔬的味道。夜里睡觉的时候,奶奶把我们的脚或夹在她的腋下,或贴肉抱在胸前。扭头将灯吹灭后,温暖便如电流,和着被子的香味,从奶奶身子里一点一点流进我们的脚底,淹没心房。
早上醒来多时,仍贪恋被温不肯起床,闭着眼睛聆听厨房里叮叮咚咚。温暖的饭香一阵阵飘来,好似看得见白色蒸气正在锅面上袅袅。奶奶把饭锅盖好,就移动着一双裹过的小脚,悄悄来到床前,一双大手伸进被子里摸索,“这是三丫头?二丫头?”我们忍住笑,悄悄把身子往里缩。终于被奶奶捉到,幼嫩的肌肤碰触到粗糙的老茧,痒痒难禁,忍不住扑哧一笑,泄露了身份。奶奶也笑起来,扬起巴掌装作要打:“鬼丫头,尽哄我,快起来!”眼里声里,都是无尽的欢喜慈爱。
我笑闹着捉住奶奶的手。奶奶就把我的手夹在两手中搓着,爱怜地说:“三 丫头手好长一个个,好尖。”
“长好不好?尖好不好?”
“当然好啊,秀才的手,拿笔的手呀。”
我知道奶奶是羡慕我们能读书识字,就把奶奶的手摊开去摩擦她。奶奶的手厚实又温暖,又粗糙,布满纵横交错的纹路和老茧,摩在手心里痒痒的,很舒服。奶奶就很舒心的笑,头一点一点。奶奶生这种很奇怪的病,头总是鸡啄米似的一点一点,你看着她累,她自己一点不知道自己在点头,也不知道疲倦。从哪一年开始这样,你问她她也不知道。她总是爱笑,笑容老菊花一样,随着她的头一点一点,都活起来。
等到大一些,便渐渐离开奶奶,开始同母亲睡。母亲的雕花木床比奶奶的床漂亮,那是她做新娘的嫁妆。床顶四周覆以木制的雕花帷幛,雕刻的是喜鹃闹枝的图案,红花绿叶相衬。雕刻精细,颜色艳丽丰富,还镶嵌有许多小片的彩釉玻璃,显得贞静而喜庆。母亲白天总是同父亲一起在田地里干农活,见不到人影。只有在夜里,她才安静地坐在床沿低头纳鞋底,浓密的黑发齐及耳下,温柔的向脸庞低拢了去,在煤油灯下构成一个美丽的剪影。她不时将针在头发里擦一擦沾点油,右手在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我们姐妹仨就在床上打闹,疯得过了头,母亲会扭过头责骂我们:“不要疯了,花板都会疯掉下来了。”眼睛里却满满都是笑意。那时候,我就总忍不住要伸头到床外,仰面朝那摇摇晃晃的花板看一眼,要看它真的掉下来了没有,或者是要看看那到底是怎样的“花枝颤颤”。
母亲的被子是填心包被,洗晒过后,母亲会教我们怎样将格子包单、棉胎、填心一层层在床上铺整齐,边角折得漂漂亮亮,再拿搓好的白棉线缝起来。填心棉布上印着几排齐耳短发的妇女们高举着红红的毛泽东手册。母亲缝被子时,我喜欢趴在床沿,一个个去比较那些举红本本的女人哪个长得更漂亮。我也喜欢母亲被子洗晒干净后的香味,那同奶奶洗晒后的印花被子是一样的味道。比较着那些女人,把头埋在松软的棉被里,棉被放出的太阳的温暖与香味,便浸入了肺腑。母亲笑说:这么舒服的被子,你晚上又可以做个好梦了。
是啊。还有什么地方比温暖的被中更能安置梦境呢?
我曾多少次在母亲或者奶奶的床上,同姐姐妹妹疯闹,或者摇醒熟睡的姐姐同我演算那些极难的数学题。也曾多少次在家人都熟睡时,独自手握书卷拥被而坐。煤油灯散发着微黄的柔光,一缕青烟在玻璃灯罩口扶摇直上,煤油香味弥漫满屋。夜在窗外寂静着,激动的心灵沉浸在手握的书中,一个人惊奇、感动、微笑或者流泪。偶有风声拍打窗棂,将思绪拉回房中,才会发现房间这样小,梦想可以那样大,抵达窗外所有浩瀚无垠的未知。
可是奶奶同母亲,又做过怎样的梦呢?我一天到晚都只见她们在忙,累了一天好不容易才沾到床,只怕连梦都来不及做吧?
记得有一次跟着母亲参加表哥的婚礼,新房外面是新郎及亲朋好友喝酒呼叫的忙碌,母亲和其它姑婶却只陪着新娘坐在床沿亲切柔和地交谈,让人觉得闺房到底是另一个秘密的世界。我最喜欢那些红红绿绿的缎面被子,它们端庄的摆放在床中央,热烈喜气却又简静,比新娘更像新娘。它们正如深藏闺中的女子,也是在箱笼中藏得久了,今日终于可以浓妆艳抹跳出来,虽然不言不语,却是它的好日子,叫你只能看得到它的存在,角角落落里都是它的喜气。我见床沿坐着的母亲似乎对这闺房的一切都极熟悉和自然,忍不住偷偷想,母亲当年也是这样的吗?奶奶当年也这样吗?她们都曾同这些喜被一样美丽、温柔和羞涩过吗?我总想伸手悄悄去摸一摸那被子,可是又不敢。
两年后的春天,我再同母亲去表哥家,却只见表嫂头发蓬蓬在喂猪食。母亲叫她,她放下猪食桶,两手在围裙上擦擦要去灶里烧火煮茶,母亲叫她不要麻烦,她就站住垂着两手同母亲说话。明亮的太阳照着房前田野,照着院子里几只鸡和散乱一地的柴草,也照穿表嫂的房间这壁到那壁。喜联已褪色泛白,红花绿叶的被子也旧了,同小孩的衣服尿布在床上堆成杂乱的一团。整个的人与砖屋都坦露在日色天光里,简陋朴素毫无遮避,昨日新嫁时的羞涩喜乐转眼已是迢迢千年。我心头大震,扭头看母亲,她却那样坦然,以为一切都应当如此。
母亲也是这样,像京剧的变脸一样,从一个地主家娇羞的新嫁娘,一下子就变为了勤劳务实的主妇吗?
母亲不太讲她的过去,我只知道外公家属地主阶级,母亲因此只上到小学四年级,就再不许读书,婚姻也受影响,只能嫁给根正苗红的贫农――我的父亲。母亲说,她嫁过来时爷爷奶奶已经六十多岁(奶奶四十一岁才生下父亲),他们原住在七里湖,因战乱和洪水才逃难到这个地方,母亲嫁过来时家里还住着茅屋。我听这些,如同天书。我从小见到的母亲,每天回来都是两腿泥巴,头发蓬乱,一身的汗水,吃饭时疲惫得连端碗的力气都没有,一点也不像书上写的地主家的女儿。而奶奶从我记事起就老得只剩几根稀疏的白发,整天移动着一双小脚忙来忙去,洗衣、做饭、喂猪,照顾孙儿。我无法去想象她们年轻时会是什么样子。
直到某天我无意中走进母亲的房间,午后的斜阳从窗户照进来,尘埃浮动。在这尘埃里,光束像追光灯打在母亲无人的花板床上。白色帐幔轻挽,花板上庄严的朱红油漆已色泽暗陈,一花一叶,一鸟一虫,都寂然无声,静观岁月流转。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只有这些精细雕刻的花纹,与母亲同喜同悲,见证和珍藏了她为少女、为新妇、为母亲的所有梦想、爱恋与艰辛。
也忽然明白,无论奶奶的蓝色印花被,还是母亲的花床,以及表嫂的红绿缎面被子,都曾做过一个女儿娇羞的梦,可那些梦,经过了就藏起了。她们要做的,就是直面岁月的动荡同世事的艰辛,辛勤地劳动,把生命一代代延续,用爱守护着我们最温暖和欢快的童年,让我们无忧无虑的成长。
似乎只是一觉醒来,童年便过去了。父亲因病英年早逝,我们姊妹开始远离家乡仓皇奔波,只剩了新婚的哥哥,同身患重疾的母亲和九十多岁的奶奶在家乡相依为命。我结婚时刚参加工作,一贫如洗,但知母亲生计艰难,决计不叫母亲为我置办嫁妆,也不举办婚礼。但等到儿子出生,母亲几百里路坐车来看我,依然为我带来棉花被同一床毛毯。母亲说,奶奶知道我生了儿子特别高兴,觉得她一手带大的三丫头好了不起,都当娘了,移动着小脚在家里转来转去,要母亲给我带这样,带那样。母亲就把毛毯给奶奶看,说你摸摸,现在兴这个,我给三丫头买了这个毛毯,好长的毛。母亲说,奶奶摸着她从未见过的极其柔软的毛毯,笑得特别满足,说这个好,这个好。我忽然间就泪如泉涌,此时方明白了几千年来女子出嫁,为娘的一定要亲手为其置办被子做嫁妆,这其中所包含的全部深意。
如今,我的奶奶同母亲都已溘然长逝,她们的印花被子,雕花木床,印有毛泽东手册的花填心,都已无影无踪,无处可追寻。她们曾来过这个世界,与我朝夕相伴许多年,一日撒手离去,却这样干净彻底,一丝痕迹也不留。但她们留下爱像这盖在身上的温暖棉被,千丝万缕,细细密密都是她们曾经的呵护;她们留下了爱在我身上流淌,融融如温泉水,浸润身心。
我的一切爱与温柔,都从这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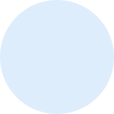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