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子皮硬铮铮,我是舅家的亲外甥,舅家门上嗮核桃 ,见我来了就收了。 舅舅说给娃一个 , 妗子说走求过。
舅舅说给娃擀长面 , 妗子说给娃热剩饭。舅舅说给娃调些油 , 妗子眼睛睁得咋个猴。
很小还不懂事的时候 ,父亲就教会我唱这首儿歌,并要我唱给妗子听。我每次到外婆家去,就给妗子唱这首歌。稚嫩的童声,天真无邪的样子,常常使妗子忍俊不禁,笑逐颜开。
舅舅是哥哥,母亲是妹妹。按关中习俗,母亲的嫂子我应该叫她舅妈,只有母亲的弟媳我才叫妗子。但是外婆家一贫如洗,外祖父用嫁母亲的财礼 ,给舅舅娶了妗子。这在关中地区是很忌讳的,就因为妹先嫁哥后娶,妗子失去了我把她叫舅妈的资格。
从小妗子就喜欢我,每次到外婆家去,妗子总是把我抱了又抱,亲了又亲。稍大一些时,她就常给我擀又细又长的面条,这在那个年月,正是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已经是农村里最好的饭了 。我小时候也是调皮的不得了,疯玩,吃饭找不着人,编谎,常常把表弟表妹惹哭。却从没有看见过妗子为此嗔脸,埋怨,不高兴。连批评也是平心静气的。说来也怪,凡是妗子批评过的事就再也不犯了。这不是一次半回,一直到我懂事了都是如此。
常听母亲说,我小时候重病过一次,大夫开的药方里缺一味药,药配不齐,全家人都急成一团,妗子自告奋勇,说她在地里见过,硬是跑遍野地,河岸,荒坡,坟堆才挖到了,解了燃眉之急。
外祖父排行为五, 隔壁三爷家有一个小舅叫骡子,大我两三岁,每次到外婆家,就去和他一起玩,后来骡子舅学会了吃烟,以后妗子再也不让我和他玩了。当时我不理解很不高兴,长大后才懂得孟母三迁为择邻的道理。妗子一家都没有文化,但当我启蒙后,她让外祖父买了笔墨纸,每次到外婆家去,她都要督促我写一篇大仿才让玩。妗子一片望子成龙之心,真是用心良苦。小学毕业后,一次到外婆家去。妗子借来四爷家一个当兵的舅舅寄回的平安家信,让我读,我读完后,妗子看我一气读完,没有卡壳夹生,好像我考上状元似的,高兴的了不得,见人就夸我会念信了,妗子爱我之心真是溢于言表
外祖父去世时,为给外祖父执魂幡扯孝纤家族内意见相左。关中风俗,为逝者执幡 必须是长房长孙。有时会因特殊情况,才在近侄孙中找代替。当时因为表弟尚在襁褓,族人说应在近侄中遴选,妗子力排众议,说要我执幡。有人指责我是外甥应排除,妗子语惊四座:“外甥怎么了,他就是我儿” 。出殡时,我执幡扯纤,走在众孝子,孝侄,孝孙的最前面。当吹鼓手的哀乐奏起时,一种庄严肃穆的气氛,不由人悲从中来,顿时想起外祖父平日的慈祥和爱心,在这即将和他永别之时,亲情难舍,便号啕大哭起来。人们议论纷纷,都说:这娃没有被白疼,一时间好评一片,为妗子撑了脸 。
1963年农村搞社教运动时,村里一些人的仇富心理,硬是要把我家的成分从上中农变成漏划地主。当时周边乡镇不时有漏划地主和漏划富农传出,形势千钧一发。这些从旧社会起就不勤稼穑的人们,跃跃欲试,志在必得。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形势十分危急,母亲愁得几近崩溃,亲友避嫌不敢接近。妗子却白天劳动挣工分,夜晚在那两侧布满着乱坟岗,狡兔窟,野狐窝。足有几里路长的田间小路 上,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看望母亲,安慰母亲。这条夜路我走过一回,荒凉得让人毛骨悚然。我是念书人,接受过无神论的教育 ,尚且如此 。妗子没有文化,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亲情,绝不会有这种勇气。她就是这样不顾担惊受怕,常常夜走这条黑路,帮母亲渡过了难关。我家的成分,终究因工作组坚持按政策办事,维持上中农不变,使那些好逸恶劳的人害人之心未能得逞。
1995年母亲去世时,妗子不顾年迈体衰,坚持陪丧三天,有她老人家坐镇,让我才临事不慌,我虽是初遇丧葬大事,因她在侧,处处有了主心骨,使母亲顺利地入土为安。痛定思痛,妗子一生和母亲姑嫂情深,患难与共。她视甥如子,大爱无边,常令我感激涕零。
妗子生了九个孩子 ,成活了两男三女。然而,女嫁,媳恶,儿不养。并且常常受到儿媳的虐待,吃饭饥一顿饱一顿,儿子又很怕媳妇不敢管。妗子气不过,便了骂儿子几句,媳妇竟然说妗子是指桑骂槐,便大打出手,妗子被打得头破血流。被逼无奈,妗子只好去法院状告媳妇虐待老人。当时农村此风颇为盛行,法院为了杀一儆百,便在村里召开了现场会,媳妇以虐待罪被调解警告。但是万万没有料到,妗子的官司虽然打赢了,从此却失去了亲情, 不但换来了媳妇更加肆无忌惮的仇视,从此亲家也断了来往。妗子再也没有了告状的力气。晚年被儿女遗弃,孑然一身 ,一个人艰难度日,顿顿吃饭以开水泡馍为主。她因早年生育过多,晚年月子病尽显现出来,腿脚犹重,行动不便,拄着两根树棍勉强行动。儿女又指望不上,晚景凄凉 ,让人不忍卒看。
我退休之初,回西安小住。去看望妗子时,只见耄耋之年的老妗子,竟然睡在光板床上,床板上铺着硬纸板,顿时我的心无比的难受。情急之下,我立即把自己的床垫拉来给她铺在床上。妗子抚摸着铺在床上的床垫对我说:“儿呀,我孝顺的儿呀”!听到她这麽说,我心里很不自在,虽然妗子明明是在感动,但我却分明有着一种“负疚”的感觉,我惭愧地说:妗子,儿不孝,一辈子工作没有成绩,事没干成,庸碌一生,愧对小时候您对我的期盼,80多岁了还让您老人家睡在这光板床上,儿对不住您呀。说到这里,鼻子一酸,眼泪不由自主的滚滚落下,和妗子抱头哭泣。看着妗子行走拄着两根树棍,我不由得羞愧满面,赶紧为她买来两根拐棍换上。这以后,我隔三差五的去看望她老人家,给她送去妻子精心为她烹制的一些食物,每次去看望。离开时她都恋恋不舍,泪眼婆娑。一次我刚走出大门,就听见她放声大哭。我不忍离去,刚准备再回头去看她。门外闲坐的大婶们劝我说:别进去了,让她哭几声吧,她心里委屈呀。
2002年11月2日上午10时许,传来妗子去世的丧讯。我赶到外婆家,望着那命运多舛,坎坷一生。含辛茹苦养儿防老,却最终竹篮打水一场空盼的妗子。她那尽显沧桑,难掩其沮丧抱憾的遗容,心里百感交集。我错叫了她一辈子妗子,但我想人即使再穷困潦倒,也应该得到她原本应该有的名分,于是在这即将永诀的最后时刻,我终于大声叫了她一声——舅妈!便长泪满腮。
作者:石龙,1938年出生于陕西西安西咸新区沣东新城石家村人,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高级工程师,退休后多次在省、地级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文学作品,在《地球》杂志上发表过《金刚石》、《美哉,滚钟口》;宁夏日报上发表过《情义无价》、《缅颜难赎童年过》,先后均获得过由长庆油田与宁夏日报联合举办的“人在旅途”征文大赛中荣获三等奖,部分作品先后在宁夏日报集结的《岁月雨》一书中收录。作品《猫谜》曾在银川日报举办的征文大赛中荣获三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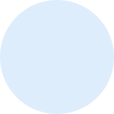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武隆籍游客专属福...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2020重庆仙女山草原...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到重庆武隆玩,这些...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真正的南国牧原!仙...



